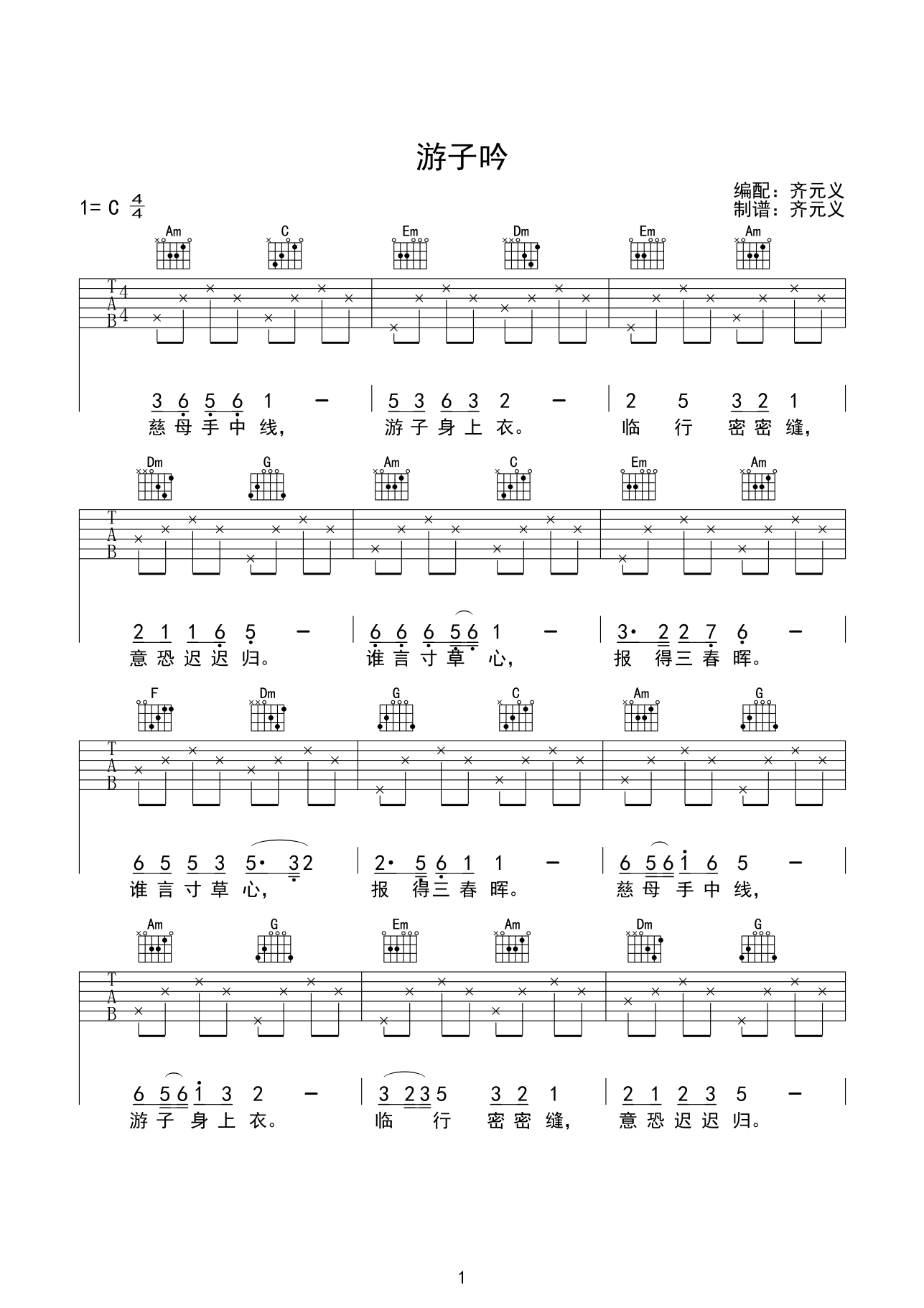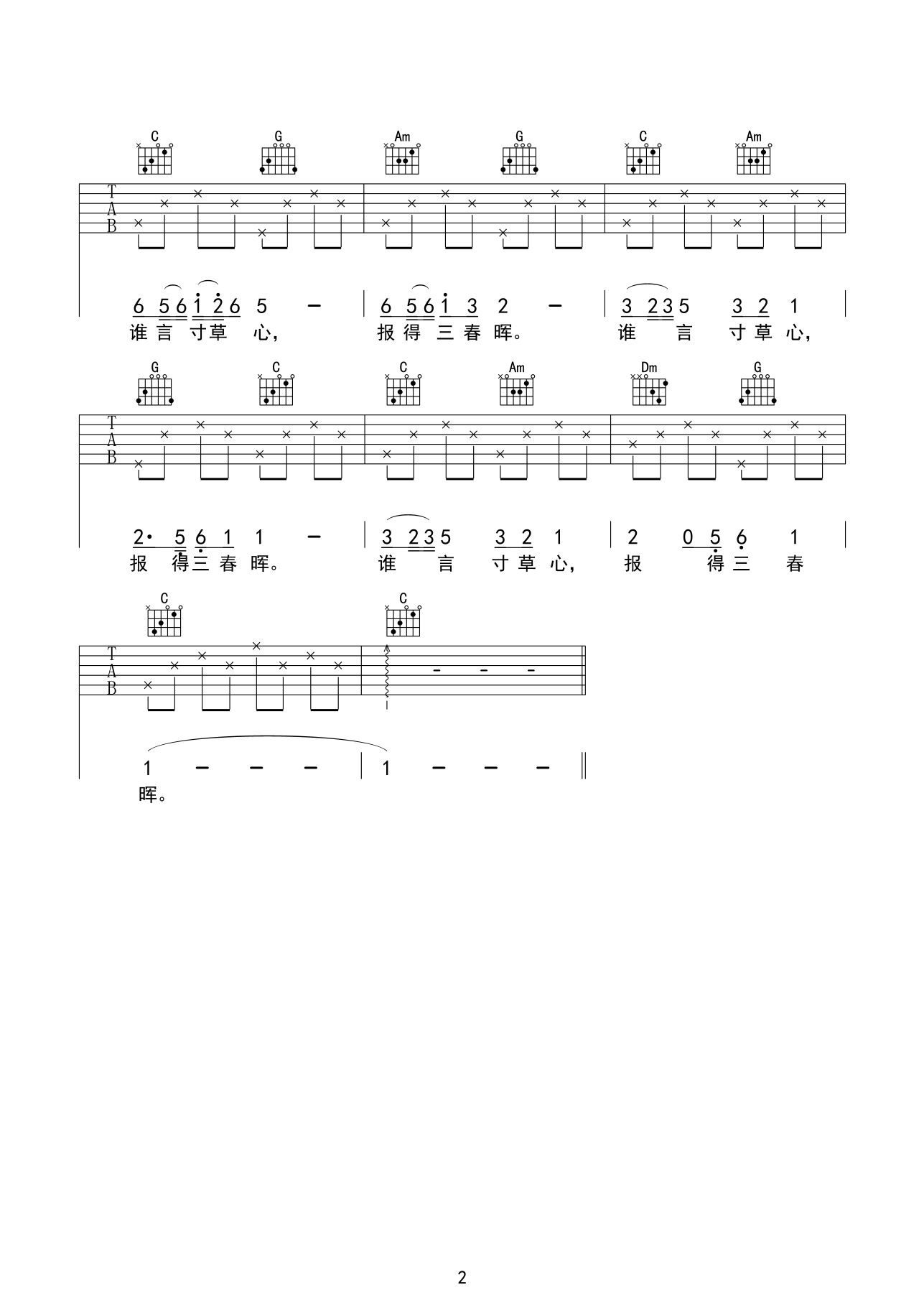《游子吟》以绵密细腻的笔触勾勒出漂泊者永恒的精神图谱,将地理位移与心灵共振编织成双重叙事。开篇“月光浸透旧行囊”的意象群构建出流动的时空剧场,磨损的票根与母亲白发形成蒙太奇式的闪回,暗示现代性迁徙中无法割断的血脉羁绊。副歌部分“故乡是脐带剪不断的痒”采用身体隐喻,将文化基因转化为生理记忆,道出离散者集体无意识中的原乡情结。第二段歌词通过“便利店冷光”“方言在舌根融化”等都市符号的堆叠,展现异质文化环境对身份认同的消解过程,而“父亲种下的樟树”作为精神坐标,则在记忆沃土中持续生长。桥段“用漂泊丈量大地经纬”将孤独感升华为存在主义式的生命勘探,行李箱轱辘声成为存在确证的节拍器。结尾处“终将走成归途”的辩证表达,既承认了当代人永恒的在路上状态,又为流动现代性提供了诗意的和解方案。全篇以具象物象承载抽象乡愁,在个人叙事中暗合全球化时代的普遍境遇,最终完成从地理乡愁到精神原乡的超越性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