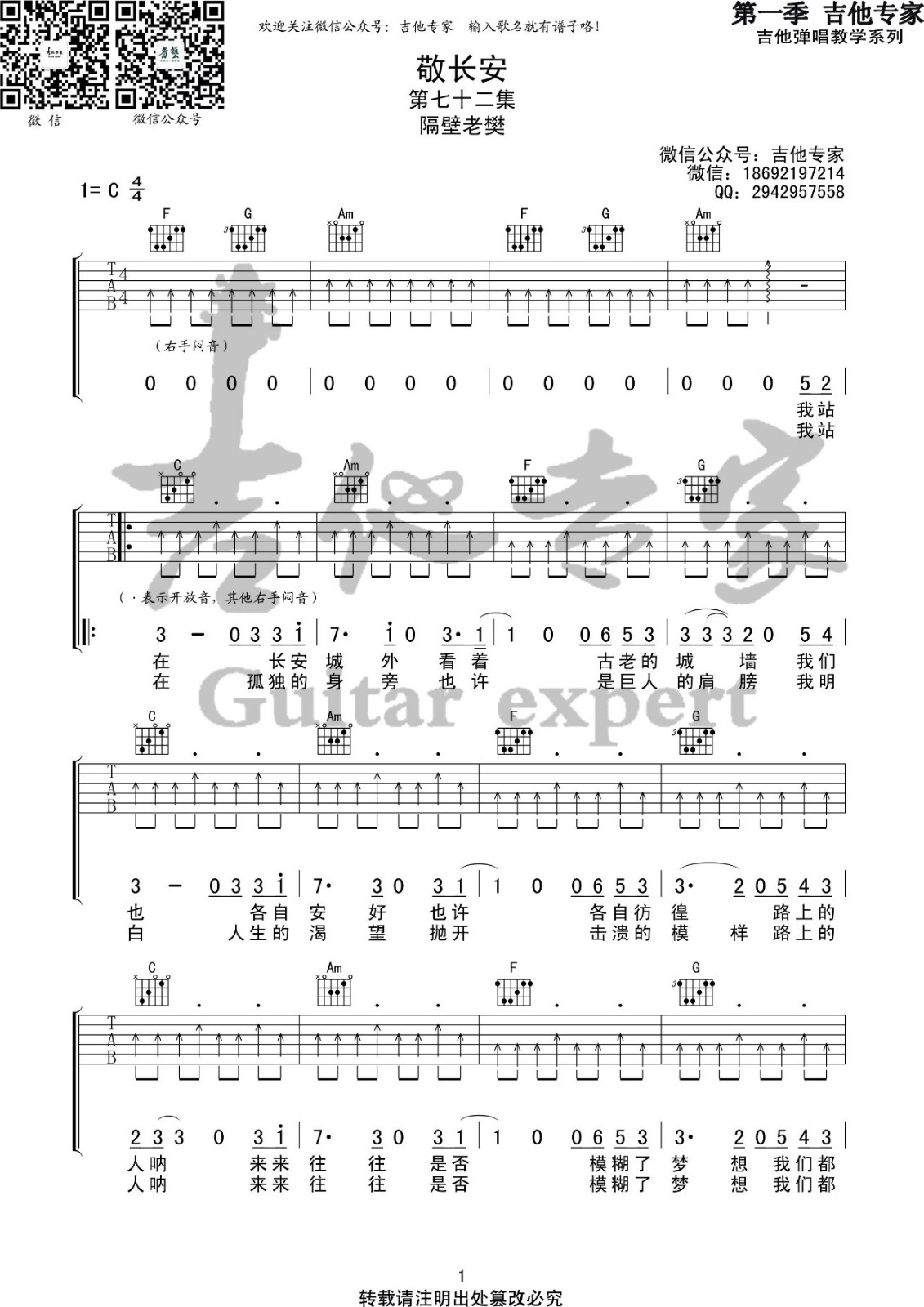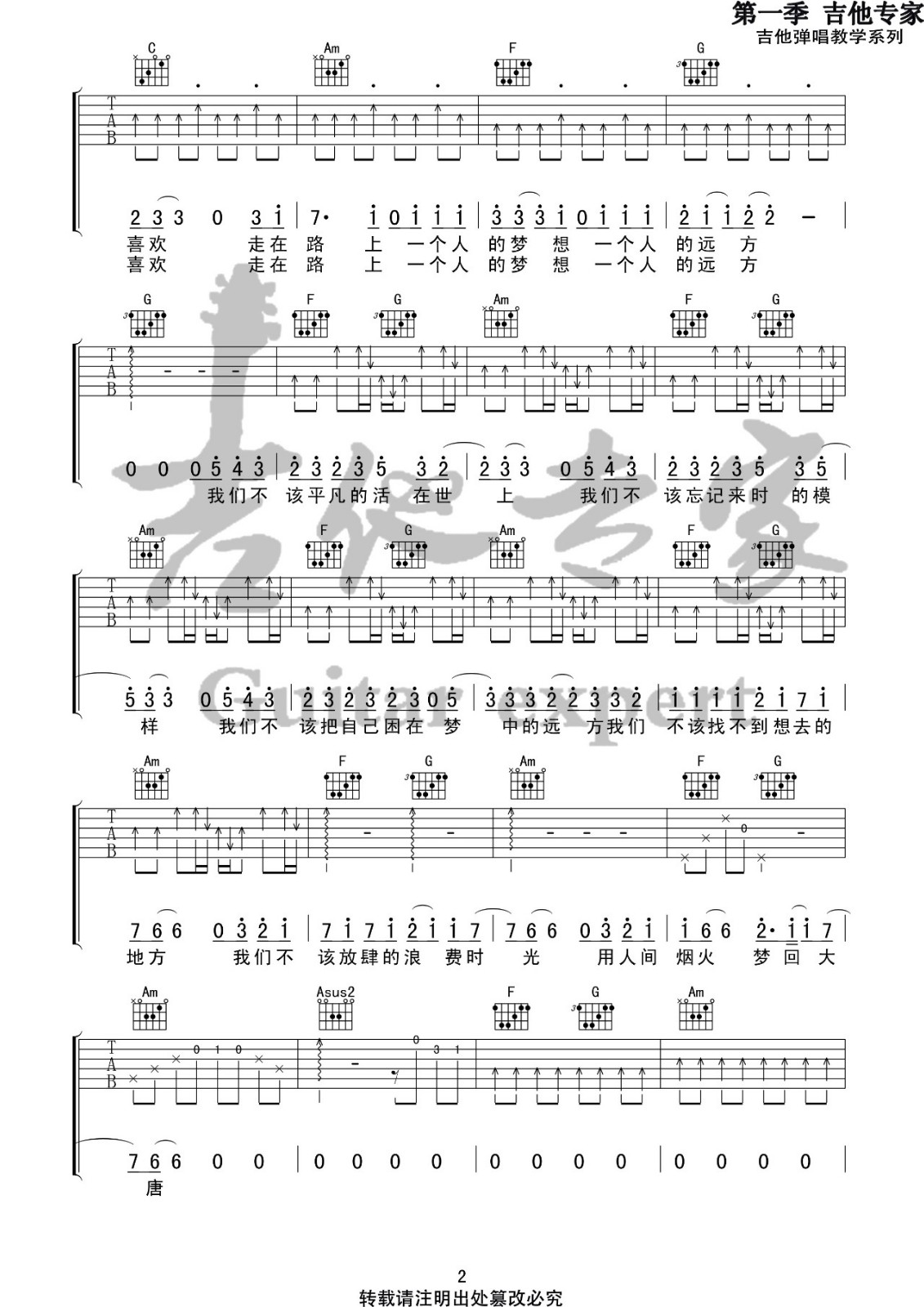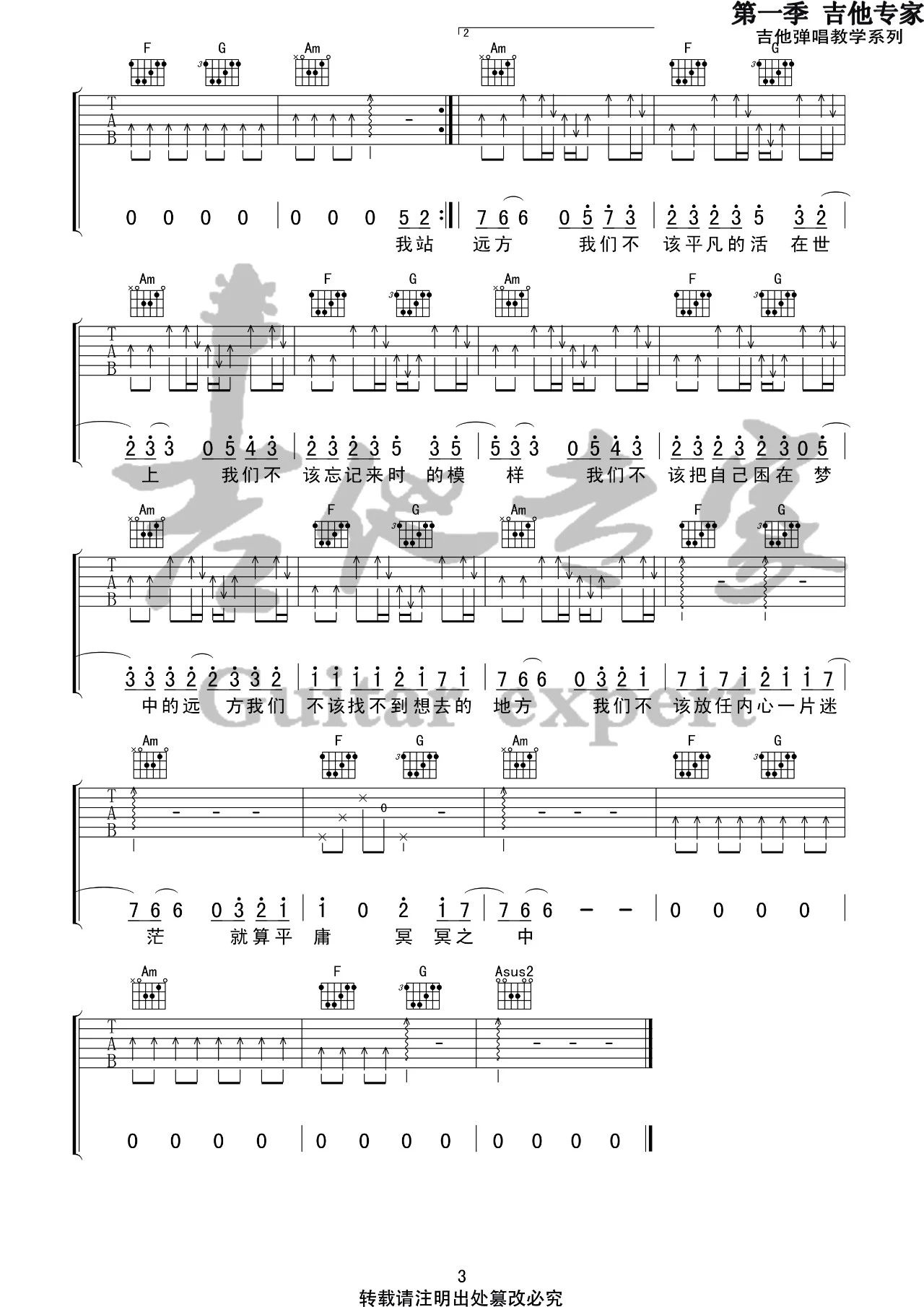《敬长安》以恢弘笔触勾勒出千年古都的沧桑与辉煌,通过时空交叠的意象群构建历史纵深。歌词将城墙砖瓦作为文明记忆的载体,"斑驳刻痕藏烽烟"既呈现物理痕迹,更暗喻民族集体记忆的层积过程。未央宫的月光与朱雀街的灯火形成时空对仗,前者凝结盛唐气象的永恒瞬间,后者延续市井烟火的生生不息,体现历史长河中变与不变的哲学思考。对"万国衣冠"的追忆不止于怀古,更暗含对开放包容精神的当代召唤,将丝绸之路的驼铃转化为文明互鉴的隐喻符号。歌词在"残阳如血"的悲壮与"华灯初上"的希冀间保持张力,既直面王朝更迭的残酷周期律,又以"春风吹又生"的顽强生命力消解历史虚无。终章"一壶浊酒敬山河"的仪式感,超越了普通的地域认同,升华为对中华文明连续性的庄严礼赞。全篇通过具象物象的蒙太奇组接,实现从物理空间到精神原型的跃迁,使长安成为所有追寻文明根脉者的精神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