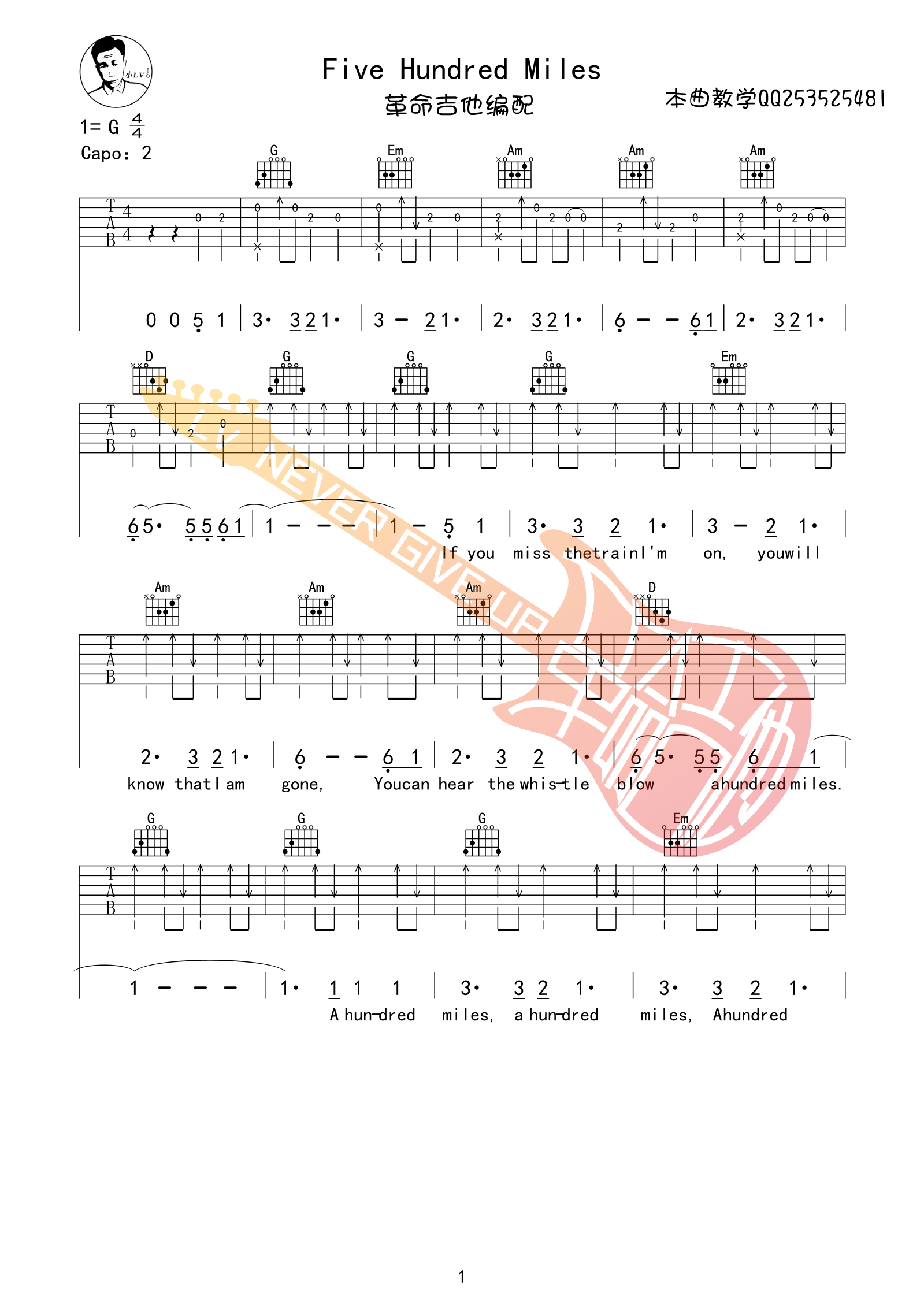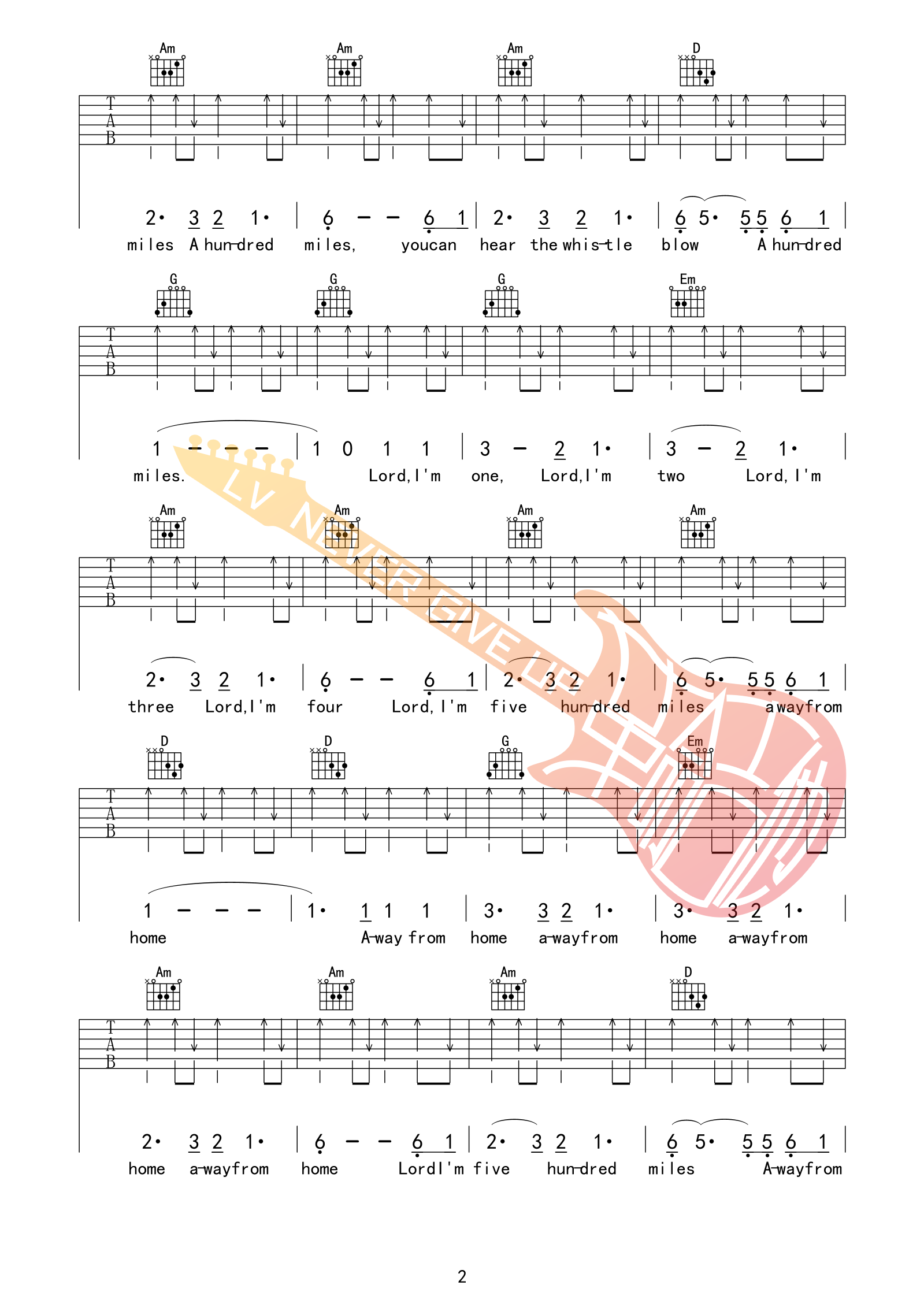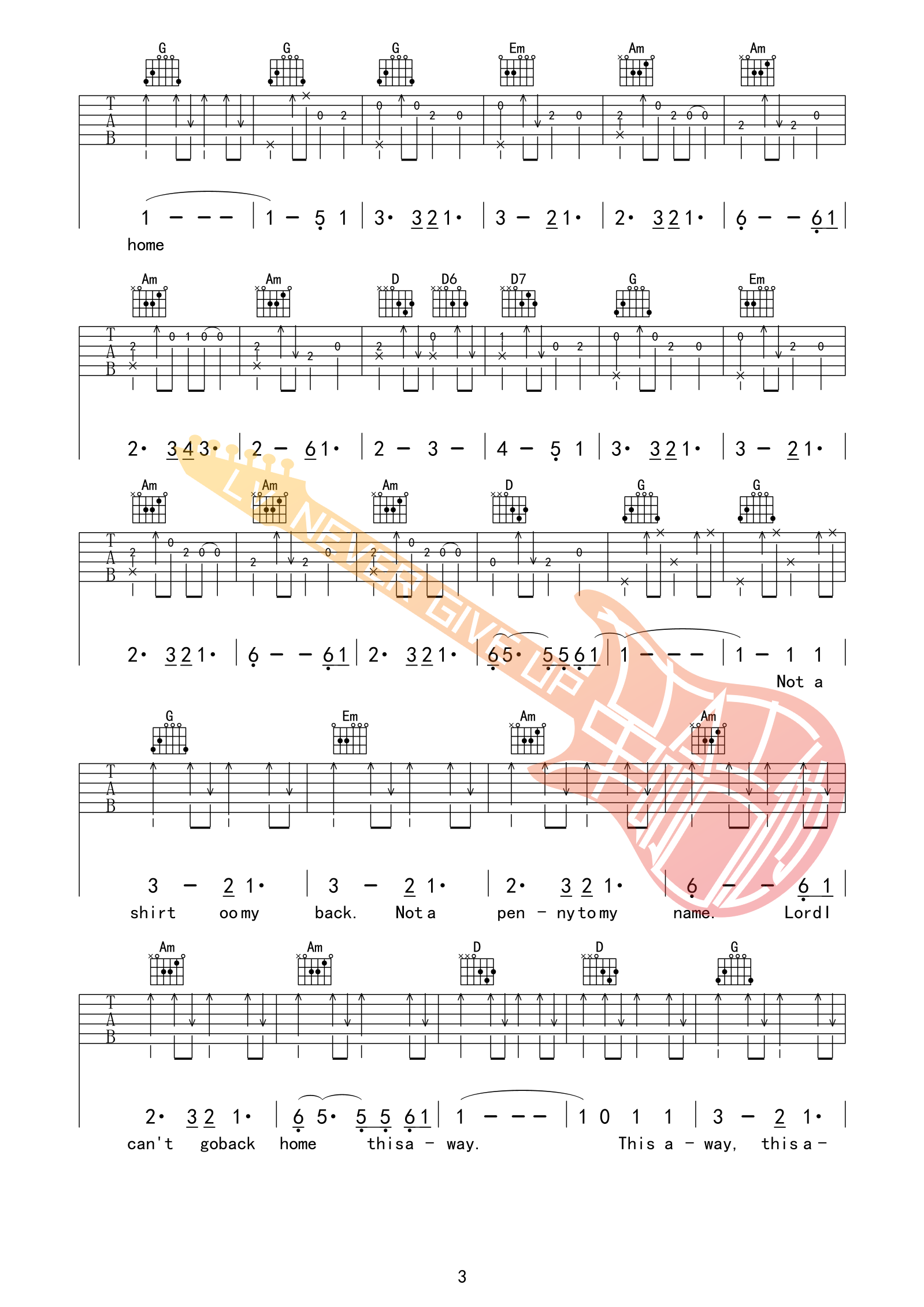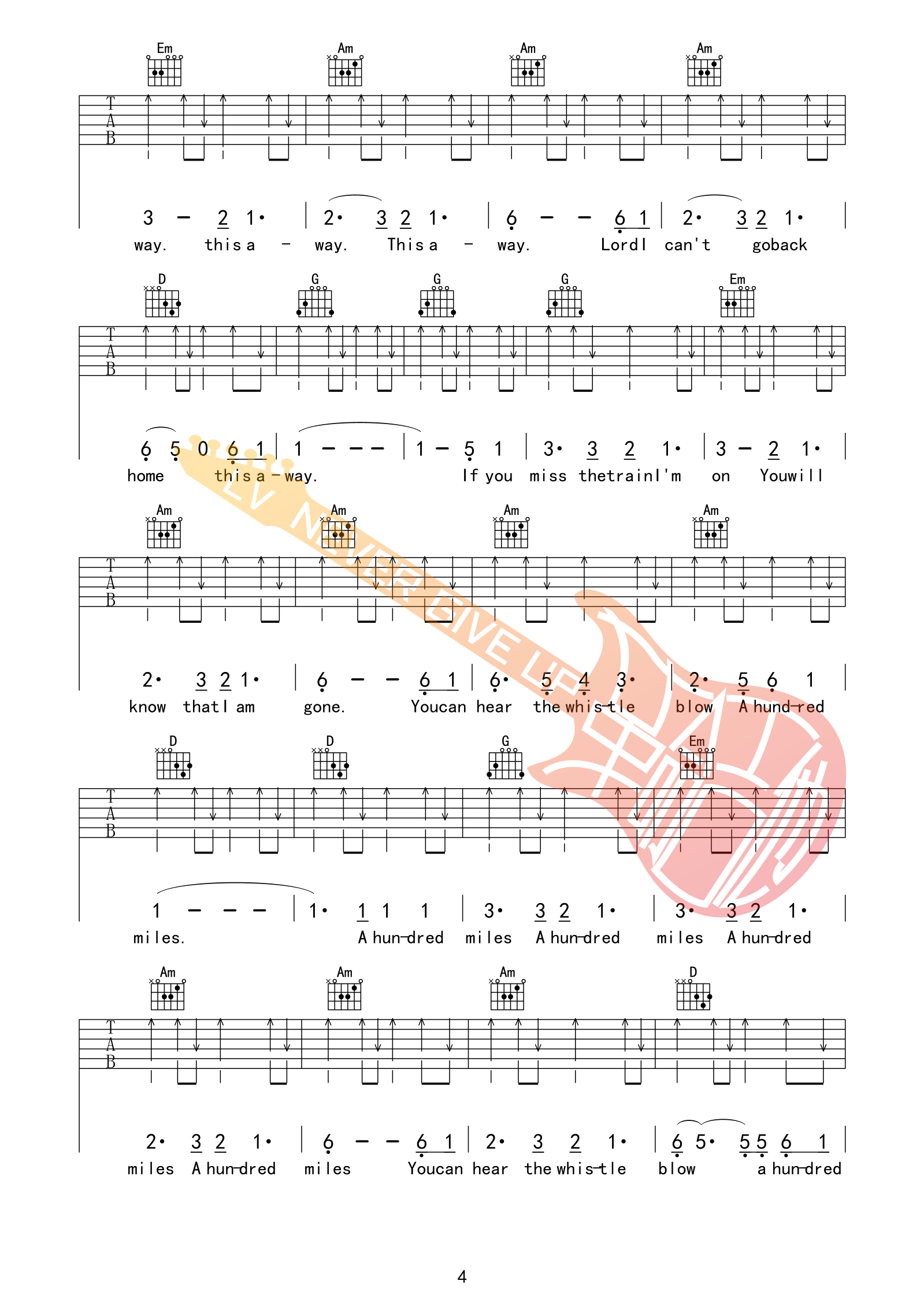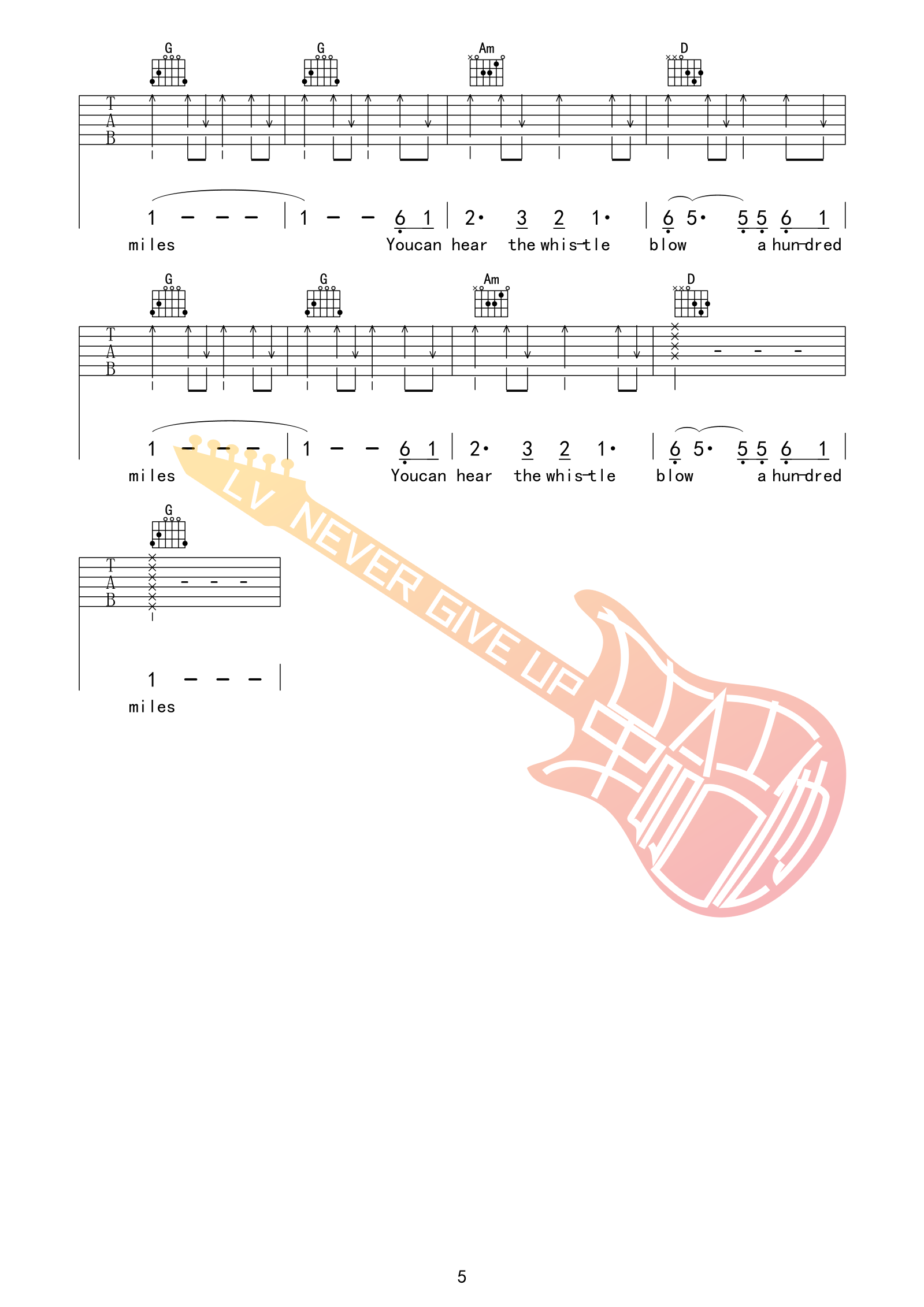《Five hundred miles》以质朴的歌词与悠扬的旋律,勾勒出一幅游子漂泊与乡愁交织的画卷。重复出现的“五百英里”既是物理距离的丈量,更是心理距离的象征,不断叠加的里程数像年轮般刻下离家的怅惘。歌词中“not a shirt on my back”与“not a penny to my name”的贫瘠意象,揭示了漂泊者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困境——衣衫褴褛的窘迫背后,是尊严被现实磨损的隐痛。火车汽笛声作为贯穿全曲的听觉符号,既代表现代文明的速度,也成为切割故乡与远方的冰冷工具,车轮与铁轨的撞击声里藏着无数未说出口的告别。副歌部分“Lord I can’t go back home this a-way”的反复咏叹,道出近乡情怯的永恒悖论:当故乡成为记忆中的标本,归途反而比离途更令人畏惧。而“a hundred miles”到“five hundred miles”的递进式咏唱,如同不断后撤的地平线,暗示人在追逐理想时与初心产生的永恒错位。这支民谣最终超越了个人叙事,成为所有异乡人的集体回声——在工业化浪潮中,每个人都是被时代列车载着前行的旅人,身后是逐渐模糊的故乡灯火,前方是永远差一张返程车票的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