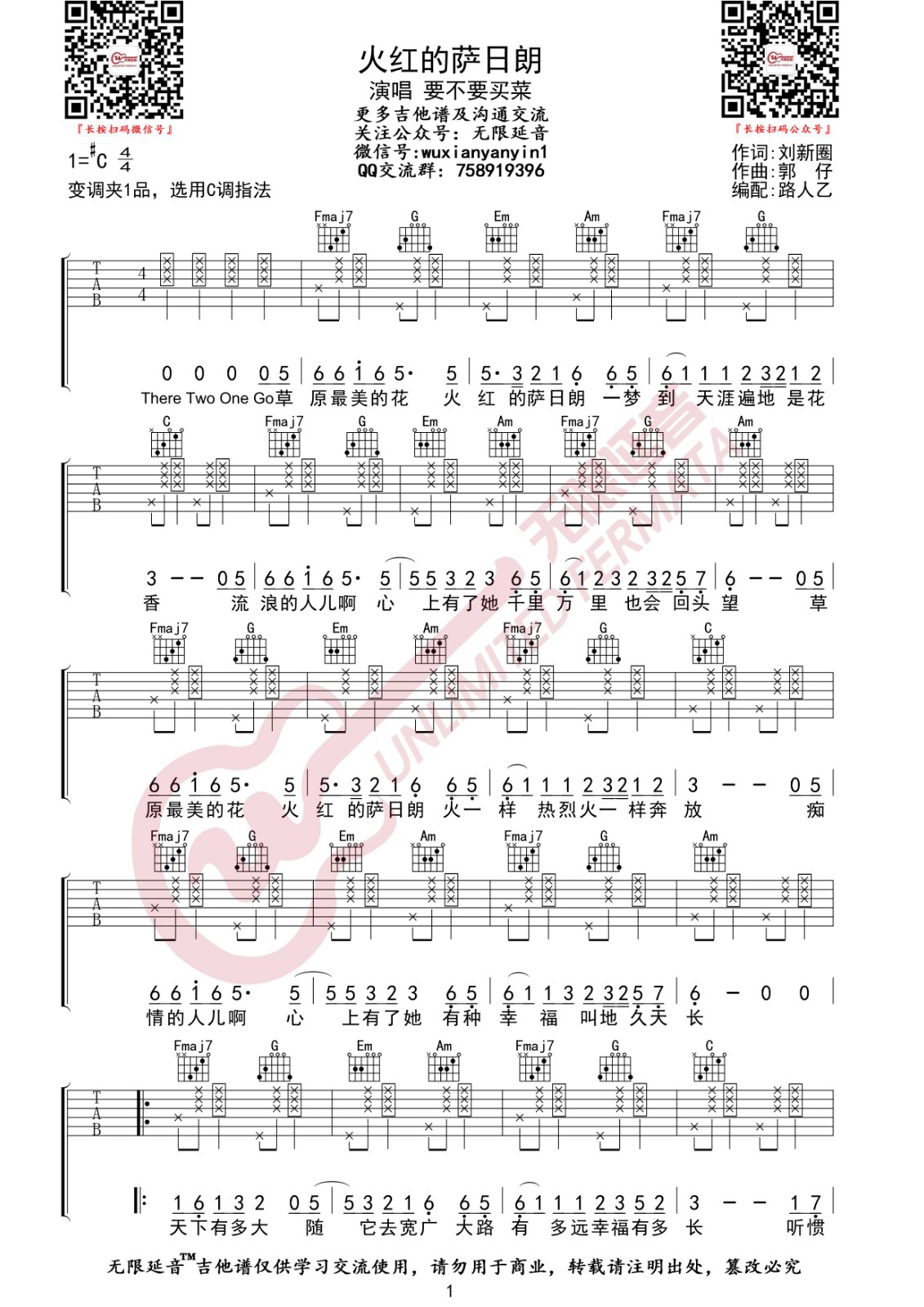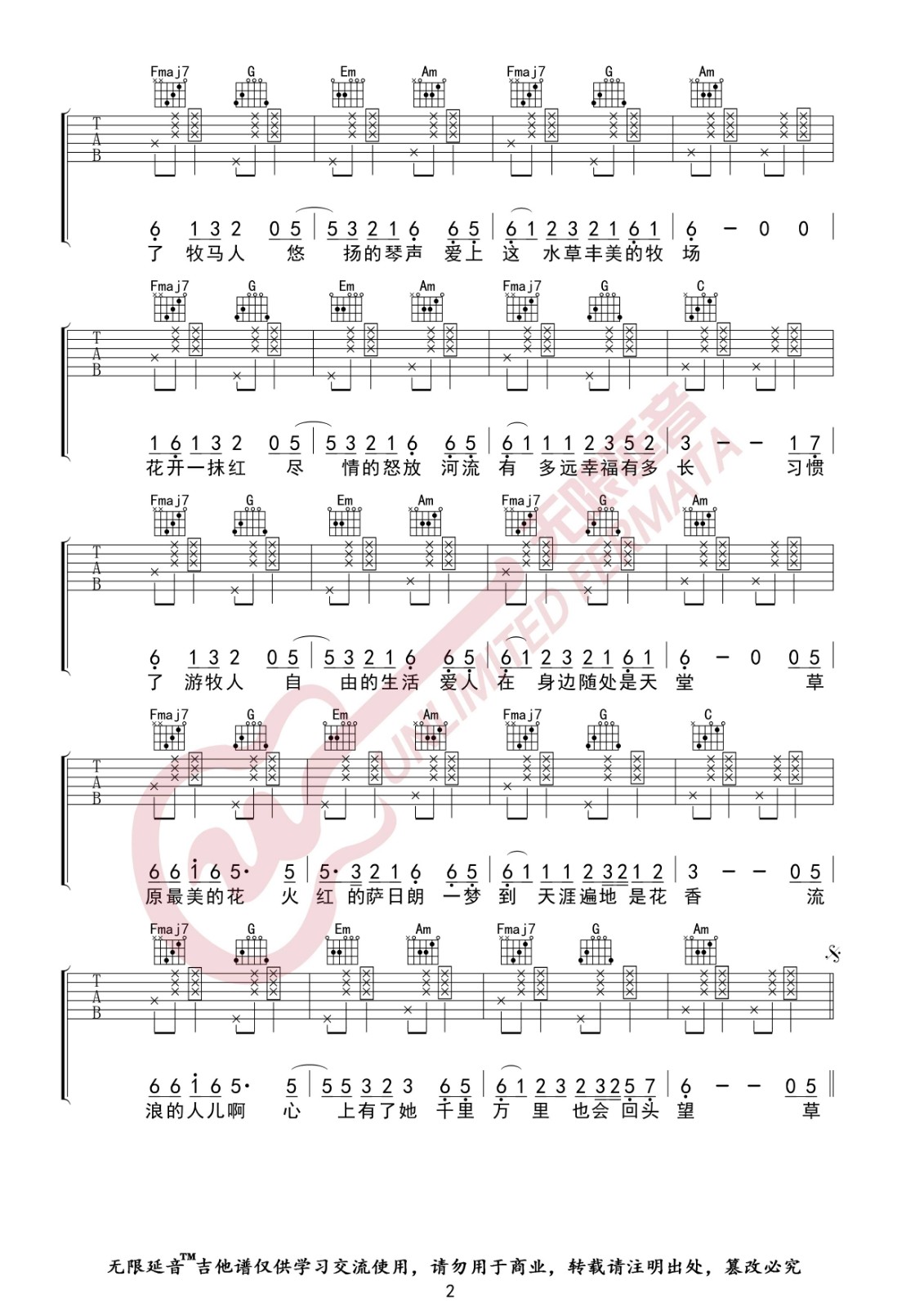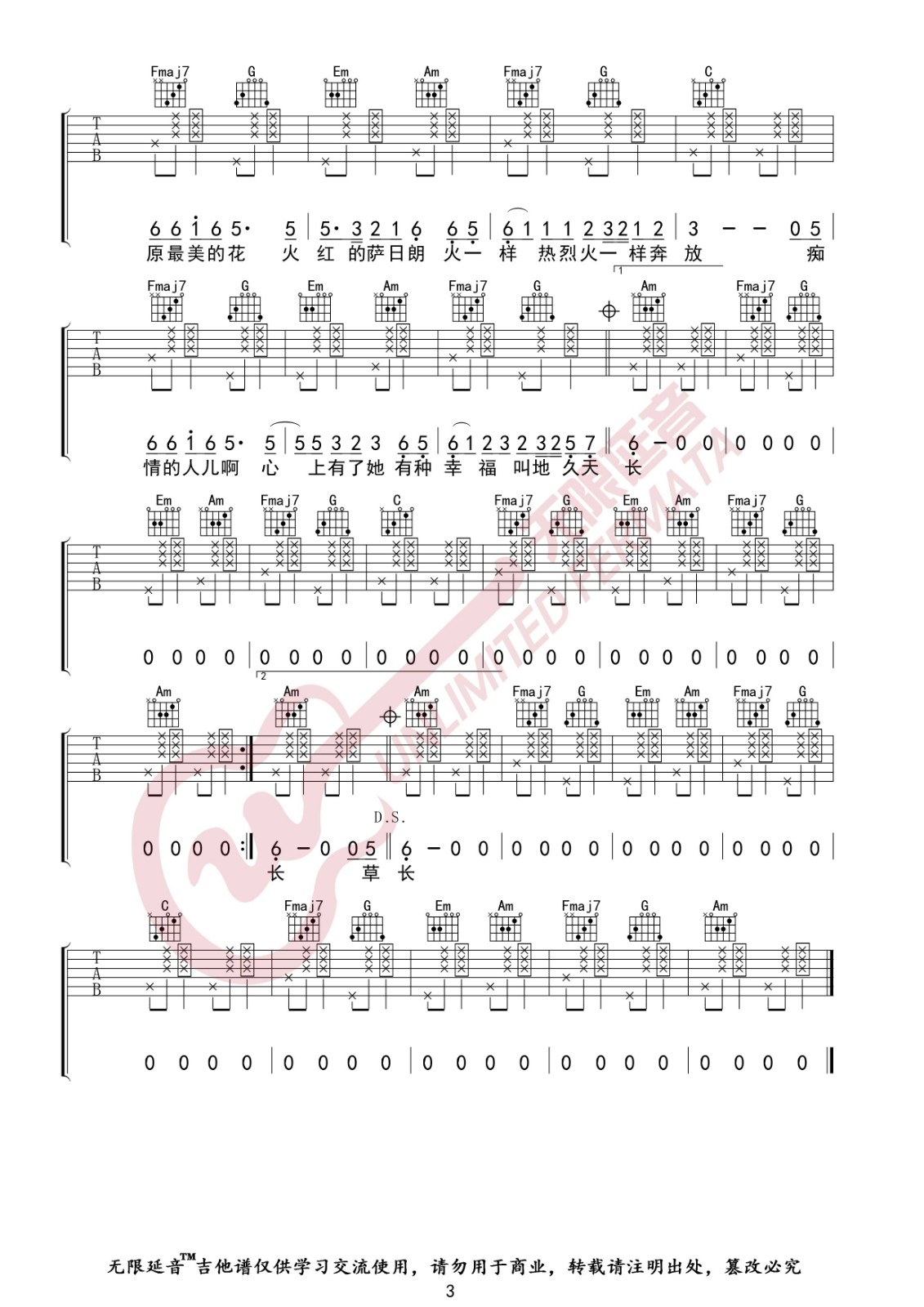《火红的萨日朗》以草原常见的萨日朗花为意象载体,通过热烈奔放的歌词语言勾勒出蒙古高原的生命图景。绛红花瓣在词中被赋予太阳的色泽,既是草原儿女对自然馈赠的礼赞,又暗喻游牧民族如火焰般炽烈的精神图腾。马蹄节奏般的韵律贯穿全篇,"踏碎晨露""追逐长风"等动态描写,将牧人与天地对话的生存哲学具象化为充满诗意的画面。歌词中反复出现的"燃烧"意象构成双重隐喻:既描绘野花在烈日下绚烂绽放的自然奇观,又象征蒙古族文化基因中永不熄灭的生命激情。对敖包、马头琴等民族符号的巧妙植入,使文字间流淌着马奶酒般的醇厚乡愁。当副歌部分以复沓句式咏叹"火红的萨日朗",实质完成了一场声音的祭祀仪式——用现代歌词重构了草原先民对自然的原始崇拜。这种炽热表达背后,藏着游牧文明对工业时代的温柔抵抗,将逐水草而居的古老智慧,转化为当代人可感知的永恒浪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