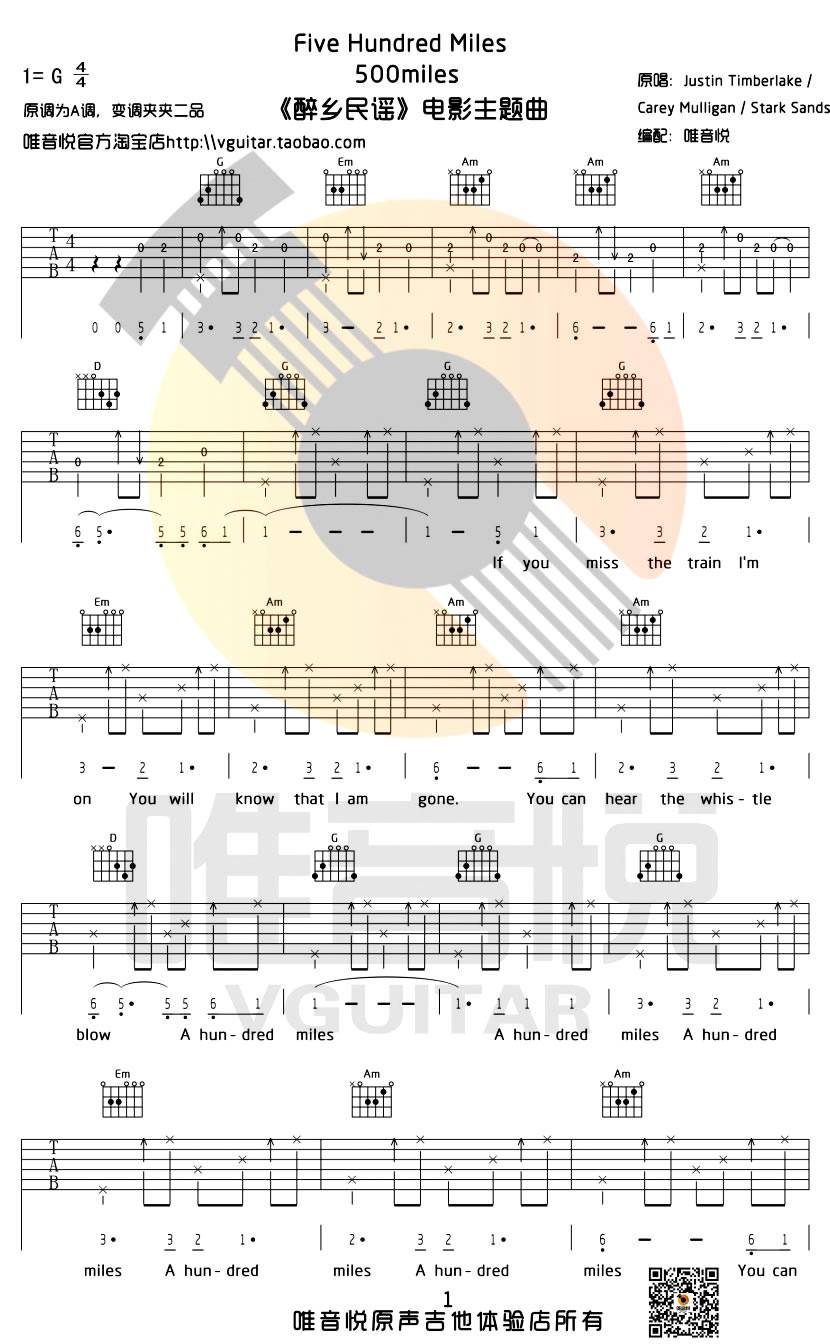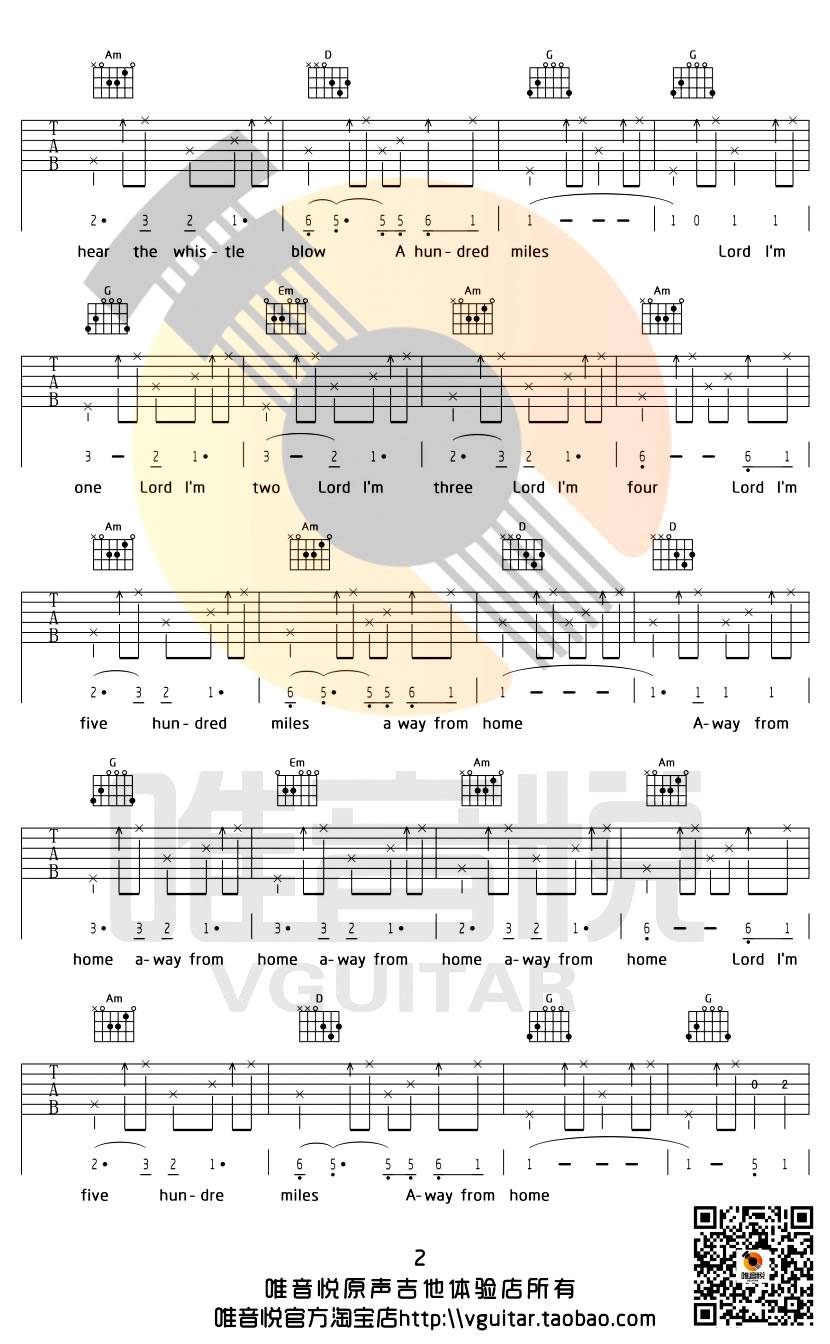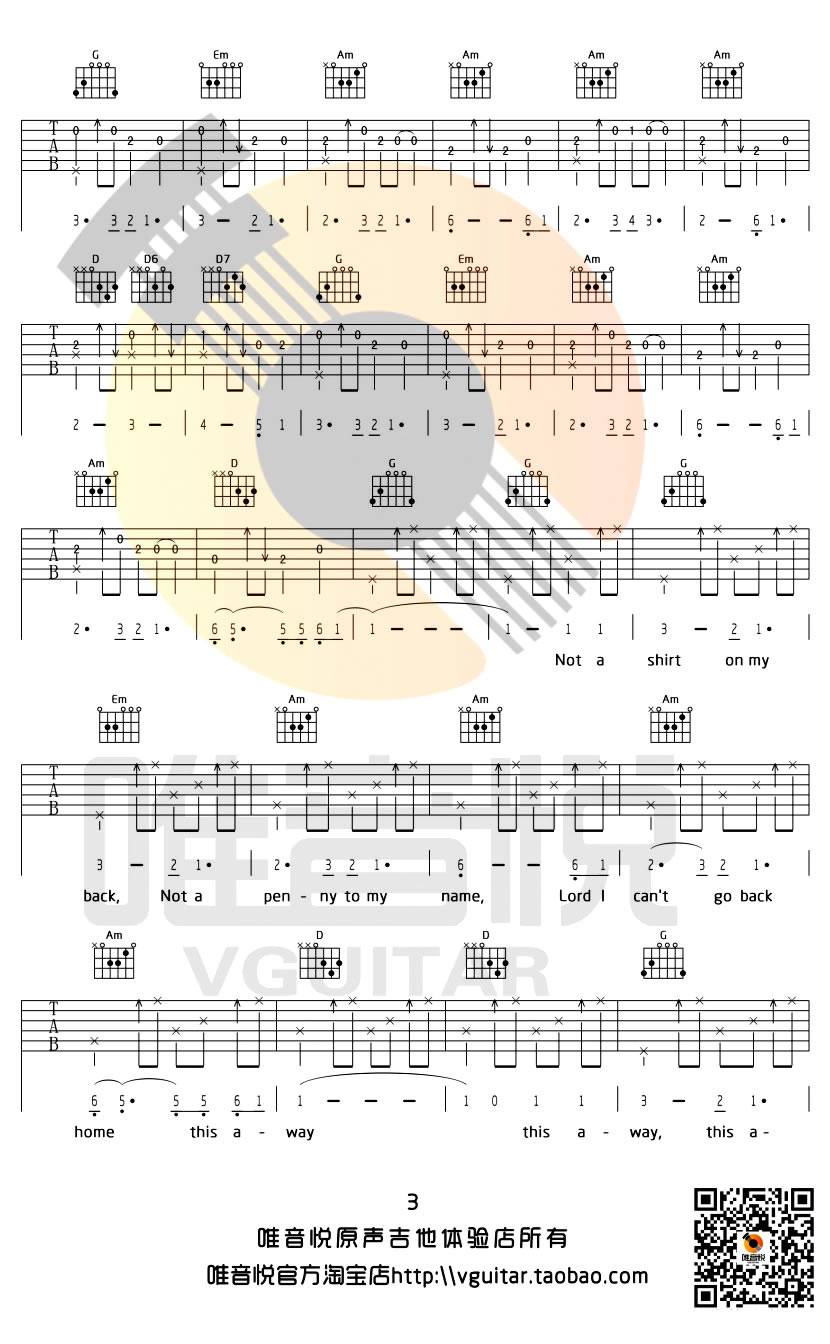《Five Hundred Miles》以简约质朴的歌词勾勒出漂泊者永恒的乡愁困境。重复出现的里程数字形成时空回环,铁轨的哐当声与汽笛鸣响编织成流动的乡愁交响,每个音符都浸染着离别的苦涩。行李箱磨损的边角记录着迁徙的轨迹,车窗外的风景不断后退,如同被距离撕扯的记忆碎片。歌词中暗藏着一个永恒的悖论:身体越是远离故土,心灵却越是贴近根源。站台上未干的泪痕与口袋里皱褶的车票形成双重见证,既证明出发的决绝,也暗示归途的渺茫。副歌部分不断叠加的里程数并非简单的距离累加,而是层层叠叠的思念沉积,最终在"Lord I'm five hundred miles away from home"的呼告中达到情感顶点。硬币在口袋叮当作响的细节,暴露出流浪者看似洒脱表象下的经济窘迫与精神困顿。这首民谣揭示的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迁徙,更是现代人普遍的精神状态——我们都在不同维度上成为远离精神原乡的流浪者,铁轨延伸的方向永远指向回不去的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