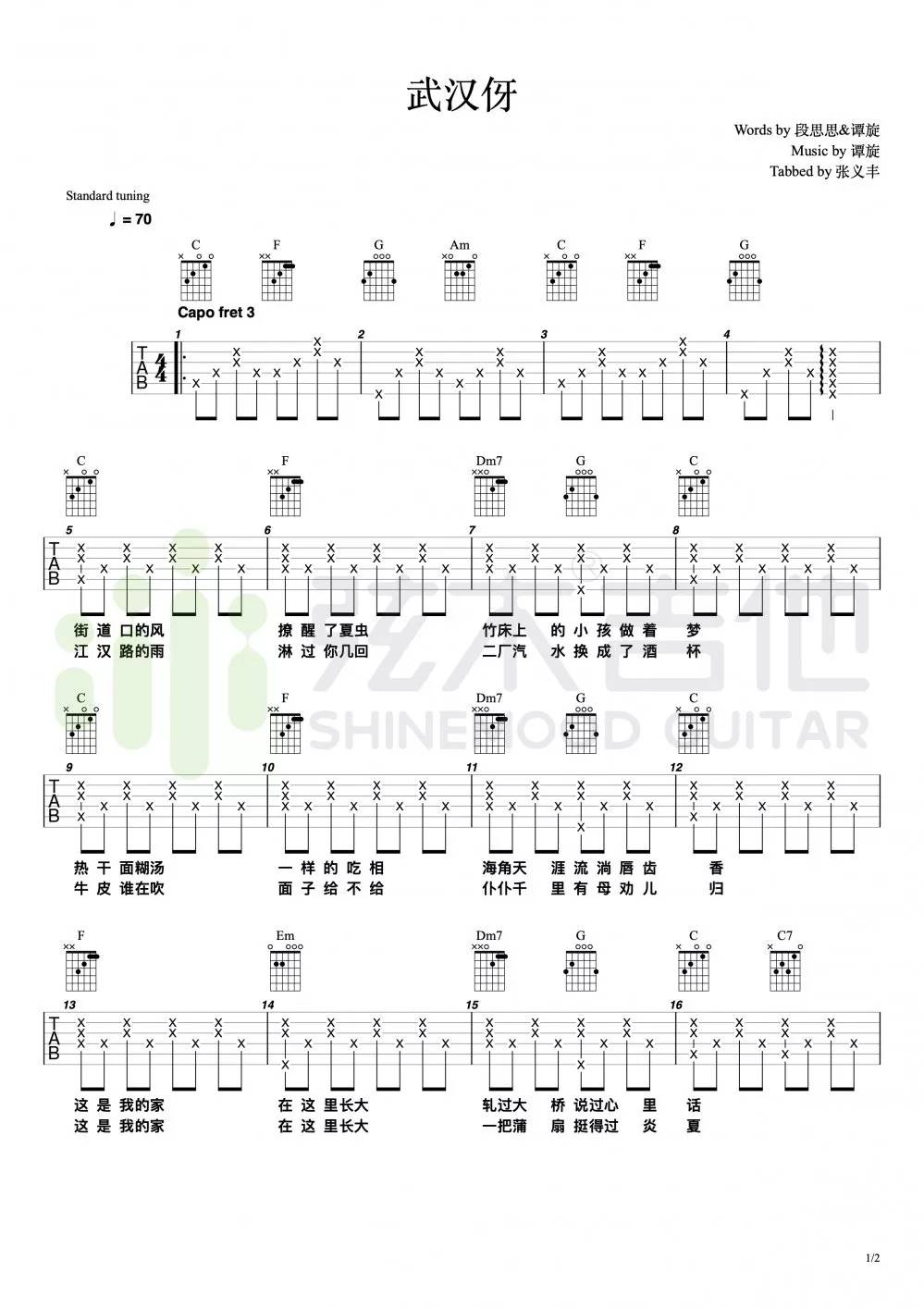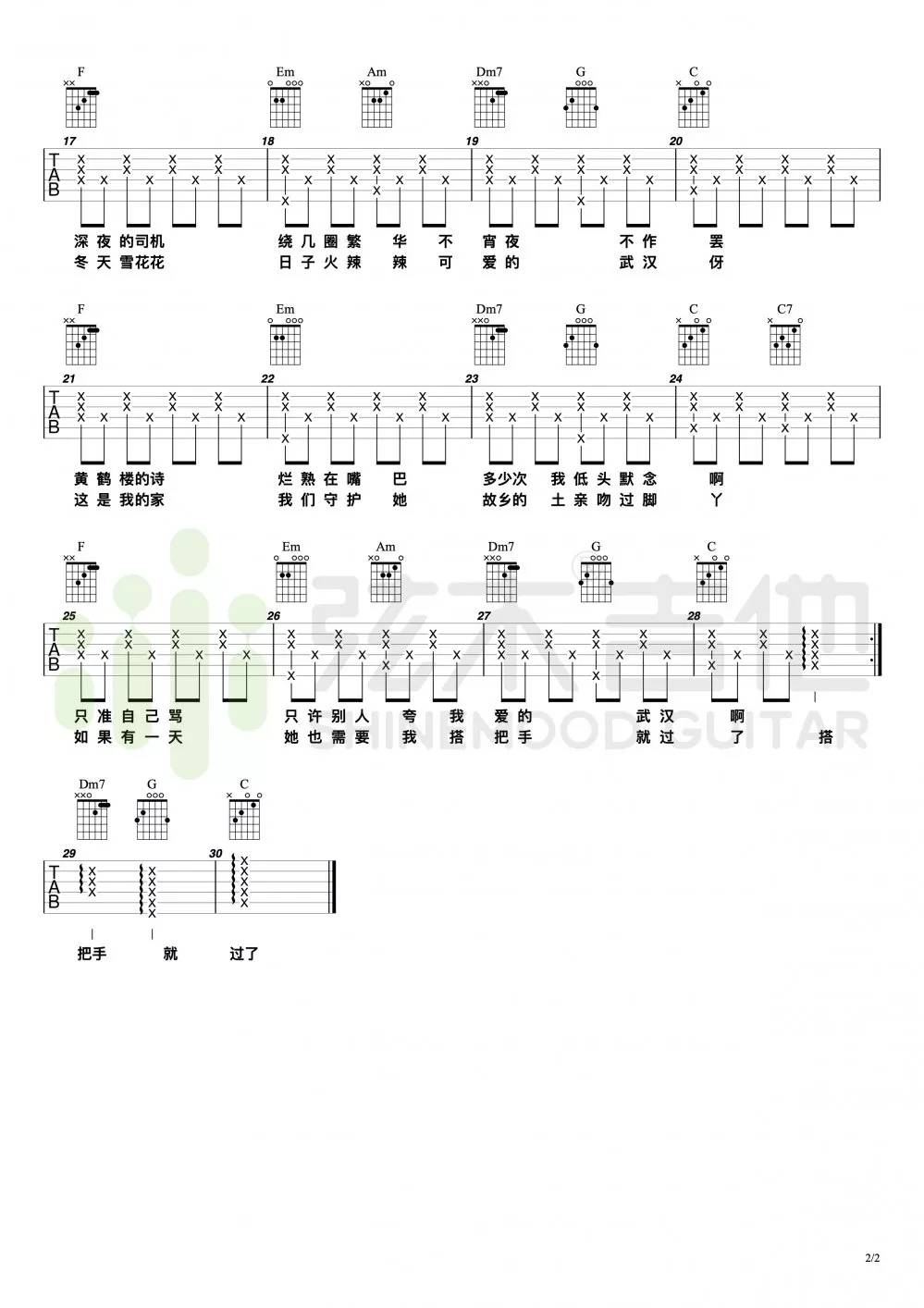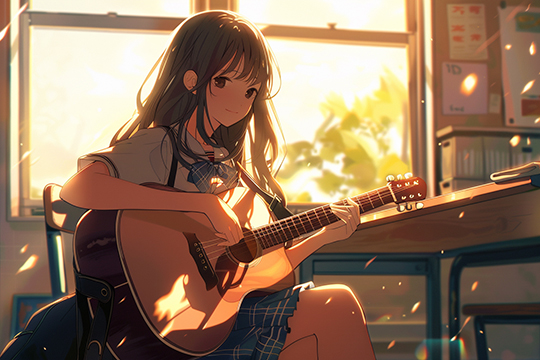



《武汉伢》以方言为载体,通过市井生活的细腻白描,构建了一座城市的精神图腾。热干面的芝麻香与江汉路的霓虹不再是简单的物象,而是转化为承载集体记忆的文化符号,将地域特色升华为情感共鸣的介质。歌词中"过早"的烟火气与长江大桥的工业美学形成微观与宏观的对照,隐喻着普通市民生活与城市命运的相互塑造。方言词汇的韵律感不仅保留了口耳相传的亲切,更在"铫子煨藕汤"这样的生活切片里,暗藏了代际传承的家族密码。当黄鹤楼意象出现时,已非单纯的地理坐标,而是凝结了乡愁的精神原乡,其古典意境与现代市声的碰撞,恰好诠释了武汉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既守着千年的码头文化,又迎着时代的浪潮蜕变。市井吆喝与江轮汽笛构成的声音图谱,实质是城市生命力的听觉具象,而"不服周"的方言精神,则暴露出这座城市坚韧的集体人格。这种创作不是对地域元素的简单堆砌,而是在琐碎日常中提炼出文化基因,让地方性叙事获得超越地理界限的情感穿透力,最终使城市形象在艺术重构中获得永恒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