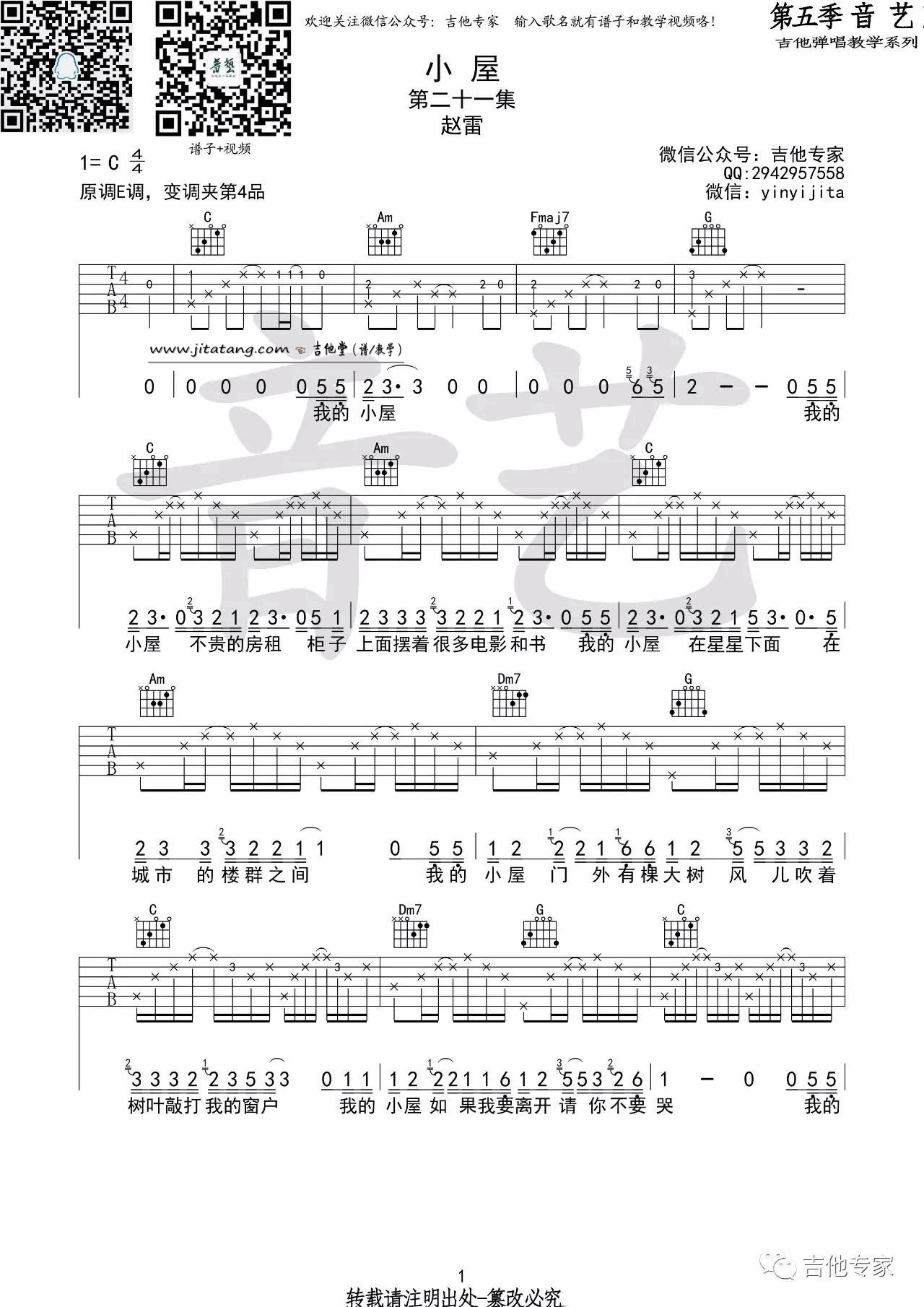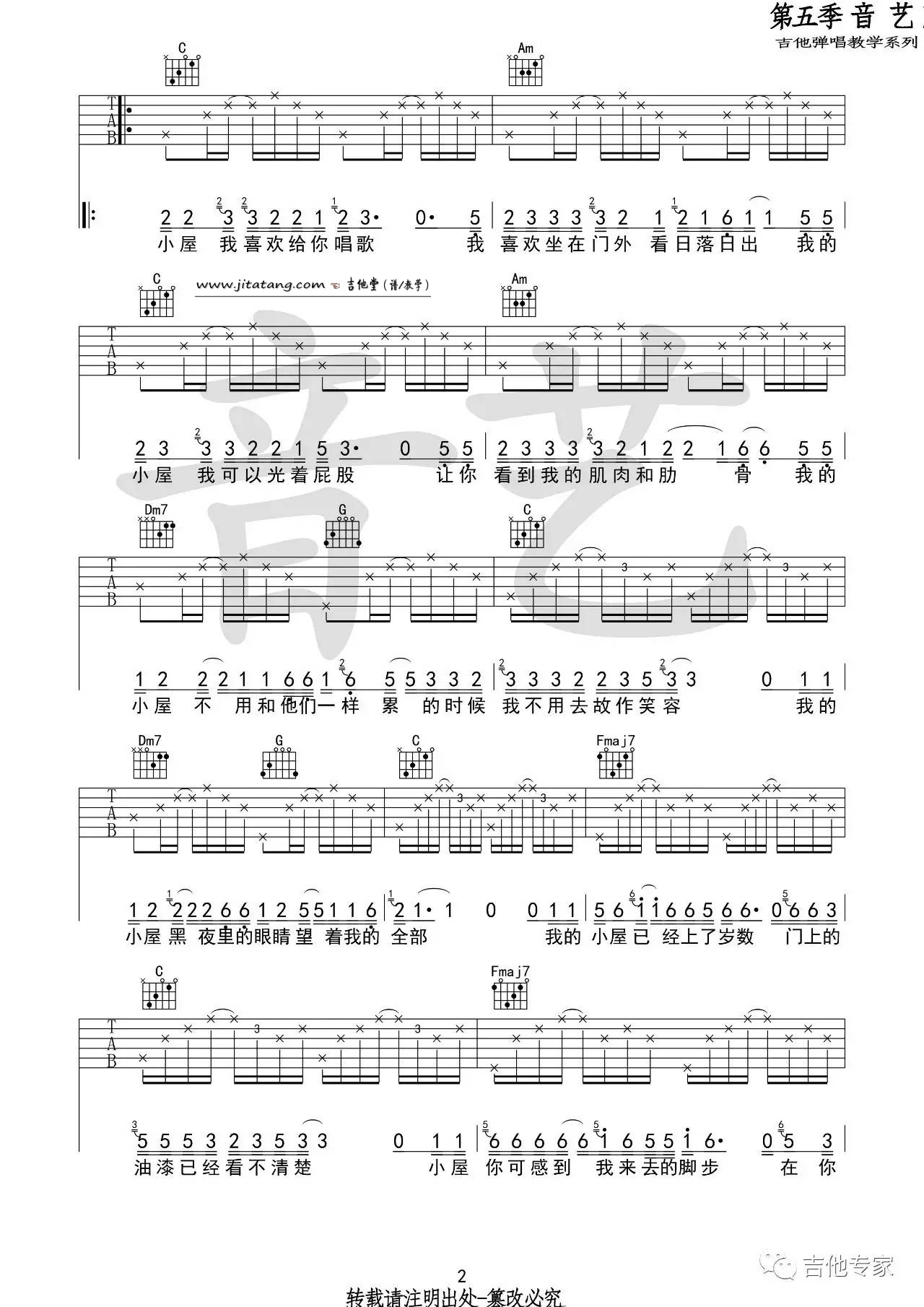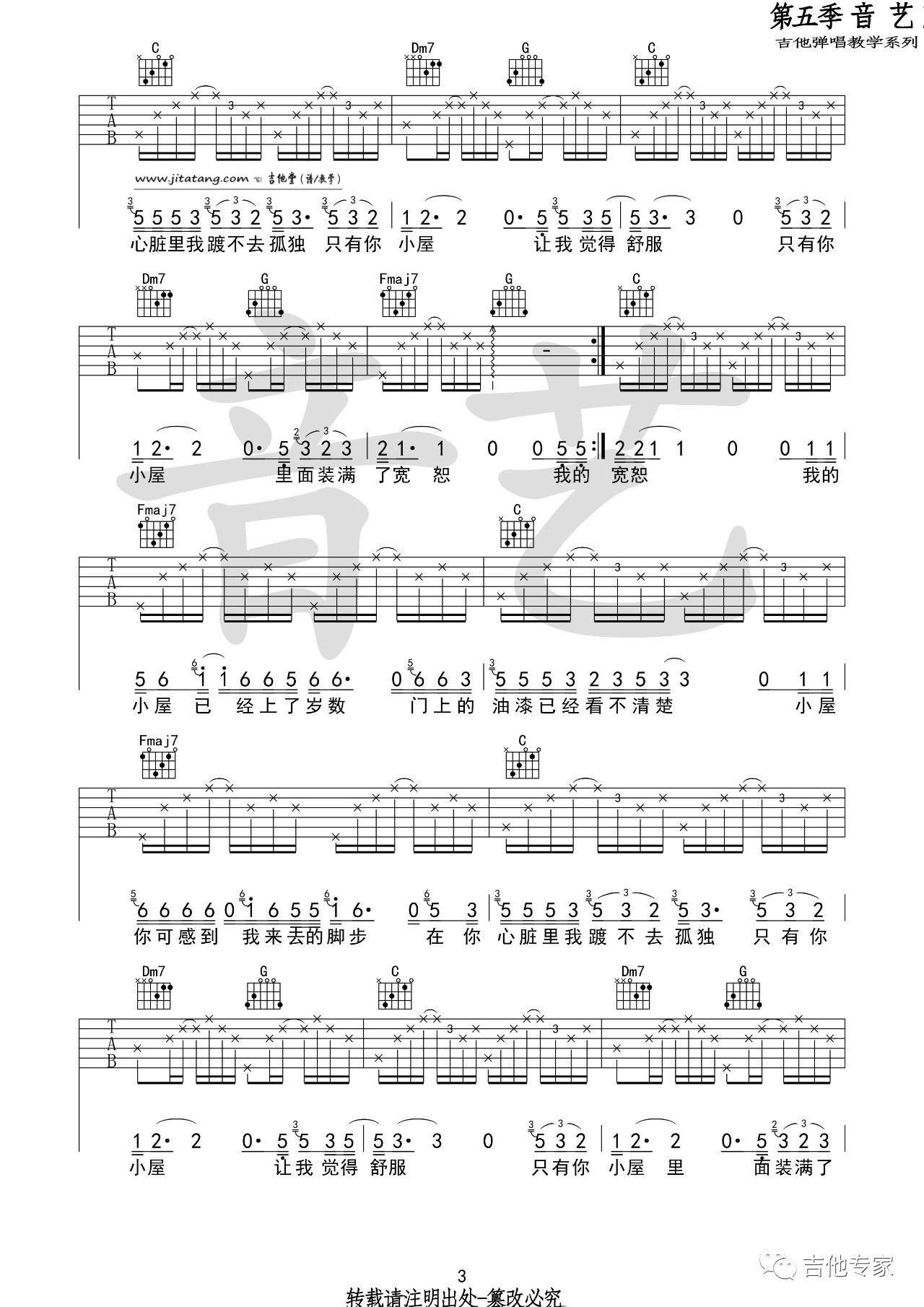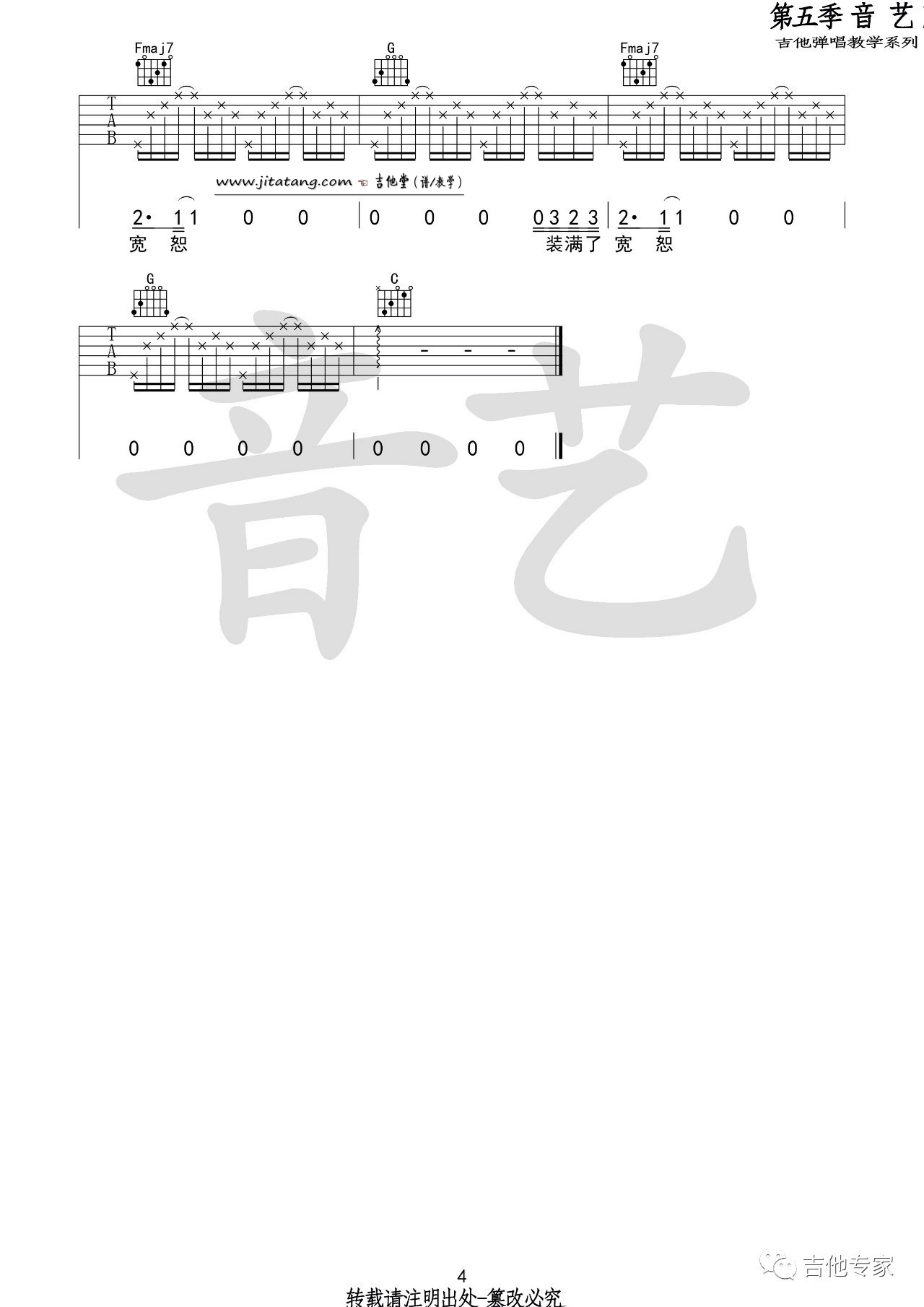《小屋》以质朴的意象勾勒出现代人精神困境与救赎的双重图景。斑驳的墙壁和倾斜的屋檐不仅是物理空间的写照,更隐喻着个体在时代洪流中的漂泊与残缺。雨水渗漏的细节暗示着外部环境对内在世界的侵蚀,而摇晃的桌椅则成为人际关系脆弱的象征。歌词中反复出现的“修补”动作,指向一种西西弗斯式的挣扎——尽管工具陈旧、双手颤抖,主体仍以近乎固执的姿态对抗着必然的消逝。这种抗争并非英雄主义的昂扬,而是糅合了疲惫与温柔的复杂状态,如同歌词中“用月光捻线”的超现实画面,揭示出人在物质匮乏中转而向诗意寻求慰藉的生存智慧。窗台上未发芽的种子作为贯穿全篇的意象,既承载着绝望中的希望投射,又保持着对希望延迟的冷静审视。最终,小屋的存在本身成为悖论的集合体:它既是束缚的牢笼,又是自由的堡垒;既是破损的实体,又是完整的精神宇宙。这种二元性恰恰解构了传统家园叙事中的理想化模式,转而呈现一种伤痕累累却依然有效的生存哲学——救赎不在远方,恰恰藏匿于持续破碎又持续重建的过程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