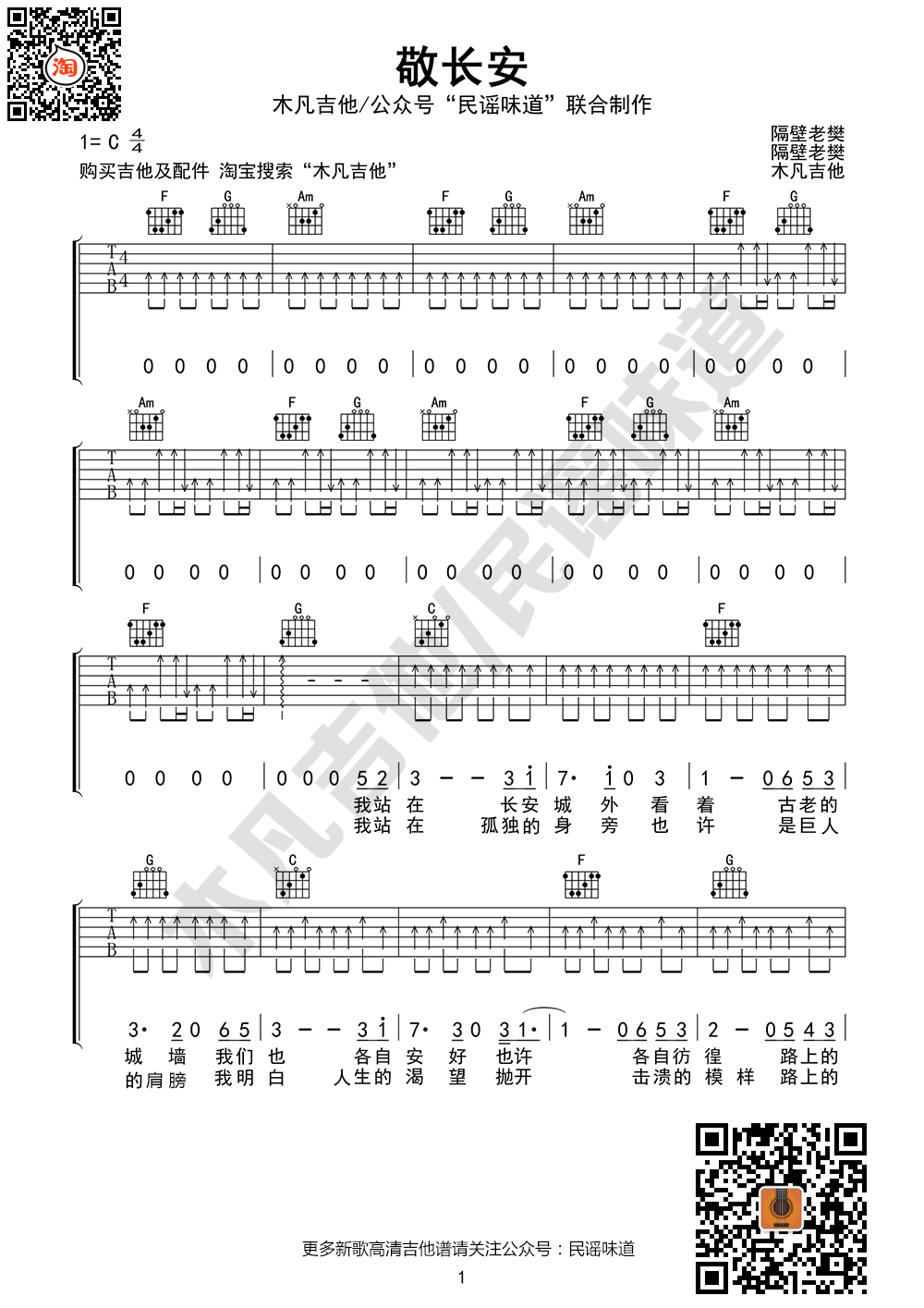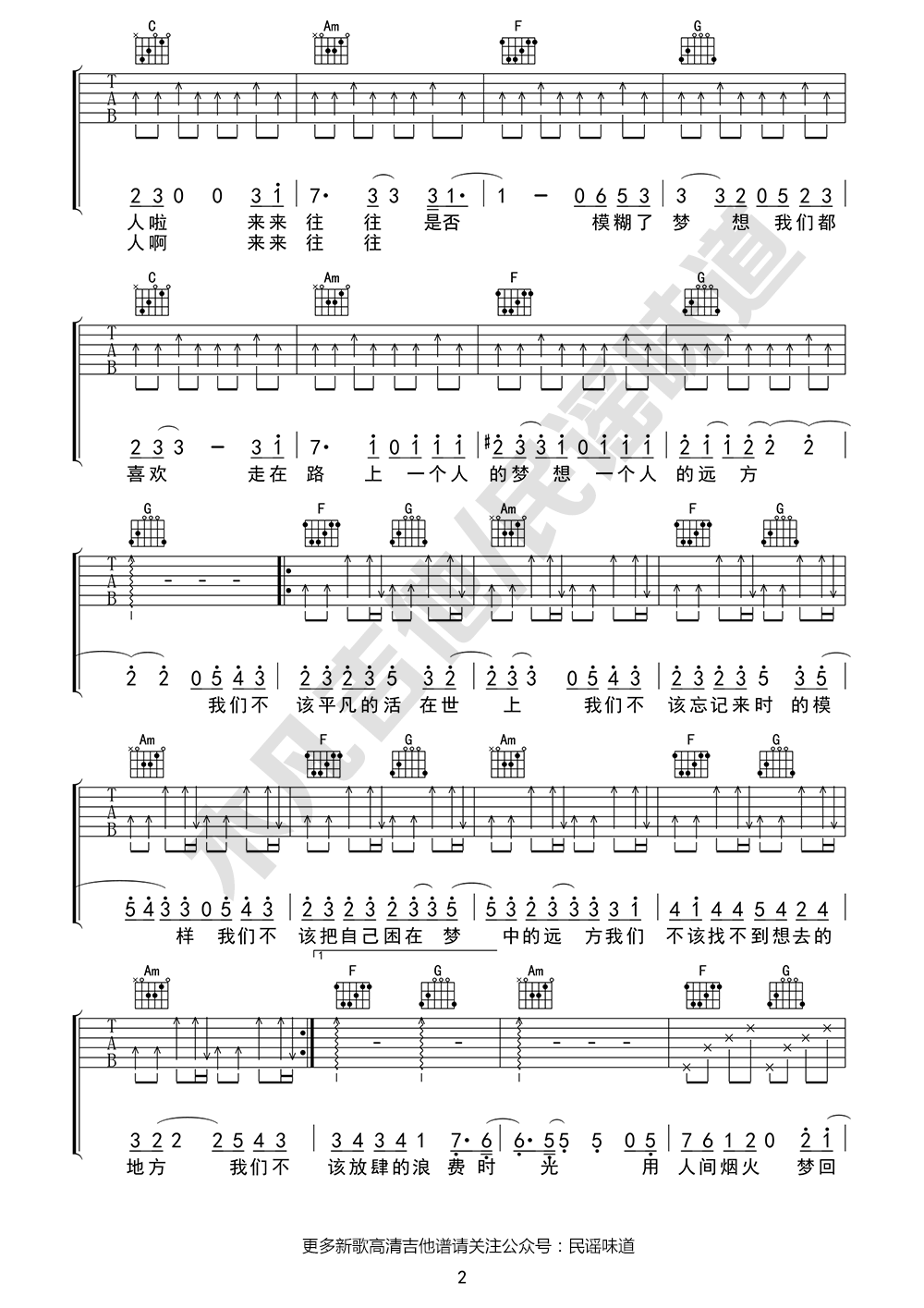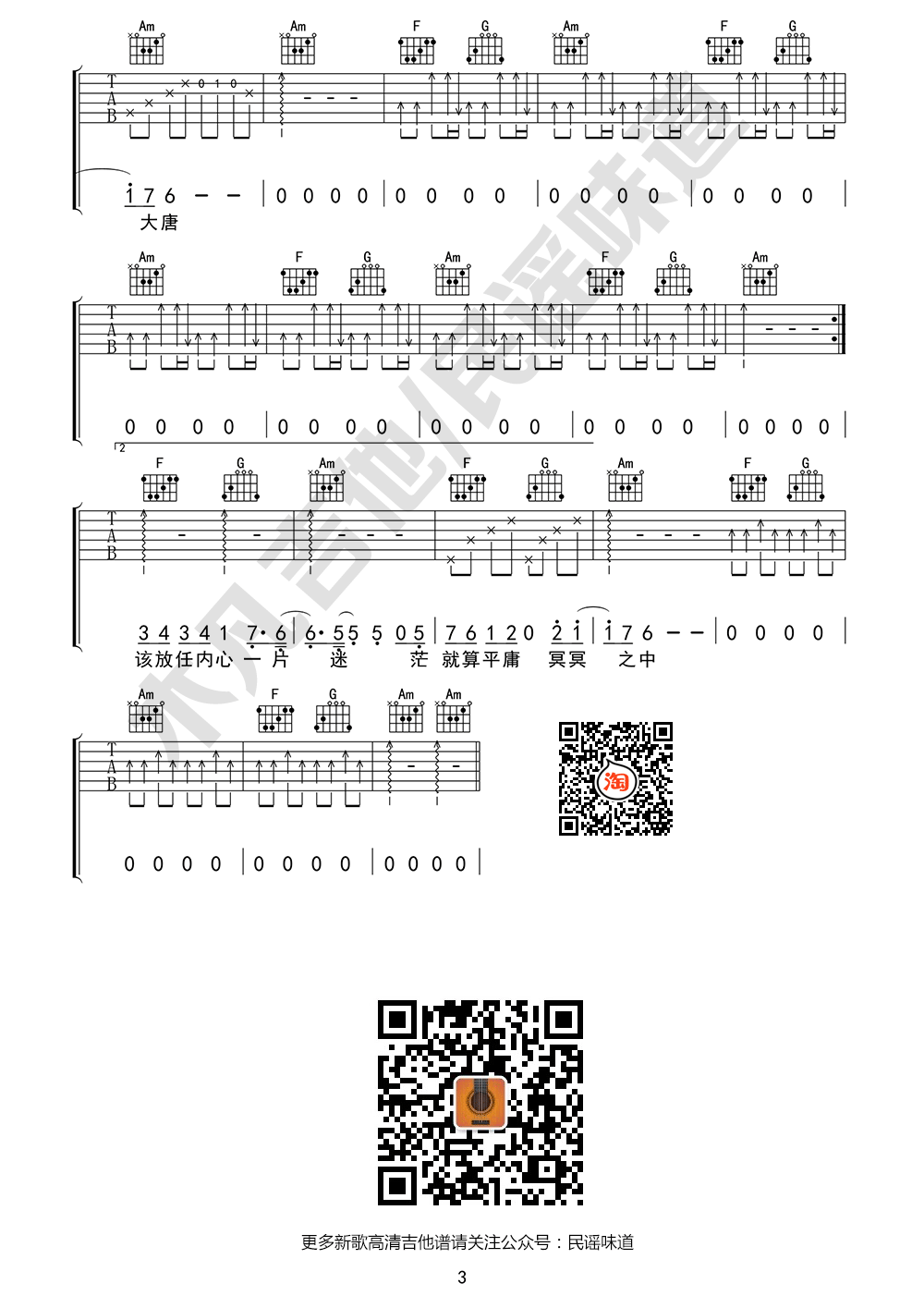《敬长安》以古都长安为意象载体,通过时空交错的笔法勾勒出历史沉淀与人间烟火的交织图景。歌词中朱墙残雪、驼铃暮云等意象既承载着十三朝古都的王朝记忆,又暗喻文明更迭中永恒与无常的辩证关系。钟鼓楼檐角悬挂的月光不仅是地理坐标,更成为穿越千年的时空见证者,折射出繁华易逝而精神不灭的文化内核。词中戍卒骨血与诗人墨痕的并置,揭示长安作为军事要塞与文化符号的双重身份,将金戈铁马的肃杀之气与诗词歌赋的温润光泽熔铸为文明传承的复合体。胡姬酒肆的琵琶声与驿马扬尘的视觉意象形成通感式书写,在声色交融中重构盛唐开放包容的气象。终章“倾酒祭山河”的仪式感,既是对消逝王朝的挽歌,更是对中华文明连续性的集体致敬。全篇通过物象的蒙太奇组接完成现代人与历史的精神对话,在废墟与新生之间探寻文明薪火相传的生命力,最终抵达超越个体生命的文化乡愁与集体记忆的深层共鸣。